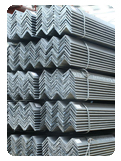“君自故鄉(xiāng)來,應(yīng)知故鄉(xiāng)事。來日綺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,每每得到與故鄉(xiāng)有關(guān)的片言只語,王摩詰的這首《雜詩·其二》,就會像潮水一般,占據(jù)我整個腦際,甚至壓抑得我喘不過氣來,黯然神傷!
人到中年,對家鄉(xiāng)的感情愈發(fā)濃烈。常常端起飯碗想起兒時的缺衣少食,看到某個景色就會聯(lián)想到故鄉(xiāng)的山水,談起家鄉(xiāng)的某件事情或某個人更是少不了普通話夾雜著方言眉飛色舞,夢里在家鄉(xiāng)的田野奔跑,用老家話的吼喊把自己驚醒都已司空見慣。每當(dāng)這個時候,就想回老家去看看,好像能夠紓解鄉(xiāng)愁的方式就是腳踏著家鄉(xiāng)的土地。
前幾日,老媽像候鳥一樣,在幾個兒女處奔波了一大圈,執(zhí)意要回到老家一個人待著,她說喜歡安靜,其實,我們姊妹幾個都知道,老媽是不想給我們添麻煩,我們過好自己的日子了,就是老媽最大的心安,最直接的幸福。
周末,一個人,走進村子里的街巷。四周靜悄悄的。幾個老人在靠大門的樹蔭下?lián)u著扇子,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閑話。待我走近,他們認(rèn)出了我,用扇子指點著和我打招呼。鄰居老王頭顫顫巍巍地起身,說都沒認(rèn)出我,老眼昏花了。我連忙扶他坐下,他說我還是個娃娃,怎么就頭發(fā)白了。五十好幾的我,在他們眼里依舊是個“娃娃”,好溫暖。
老媽知道我要回來,早早的收拾很久未用的大鐵鍋,弱小的身軀幾乎趴在鍋臺上,使勁地攪著鍋里的攪團,我連忙接過搟面杖,怨著老媽費勁做這東西。老媽抹抹額頭上的汗水,喘著粗氣說:趁媽還在,能吃上你最喜歡的攪團,就是你這個兒子最大的幸福。來,一碗燃窩攪團,再來一碗魚魚,媽再給你來點軟呱呱,辣子放紅點才香。我可勁地打著飽嗝,老媽還給我塞過來一大片金黃锃亮的呱呱,說這個幫助消化,多吃點。我用干脆的呱呱擋住我的視線,呱呱背后的我已經(jīng)淚流滿面。
幫老媽清理了一下常吃的藥,過期的給扔了,需要補充的隨手記下。把冰箱里的東西也清理了一下,老媽在旁邊一直說,沒壞還能吃。都從過年放到現(xiàn)在,已經(jīng)半年了,吃了對身體不好。把買的一大包新鮮的蔬菜和豬肉給她理好,收了曬在院子里的被子,叮囑老媽晚上早點關(guān)門,手機24小時保持暢通,身體不舒服,及時給我們姊妹打電話。
離開家的時候,街道上已經(jīng)安靜許多,那幾個諞閑傳的佝僂背影已經(jīng)消失在自己的大門里,唯有一兩只老狗,站在街邊,半信半疑地?fù)u著尾巴,打量我這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。太陽將半個臉藏進了那一排粗壯的白楊樹后面,綠樹、田野、村莊,在夕陽的余暉下變成了一幅美麗的剪影,印刻進我的腦海。
什么是故鄉(xiāng)?就是當(dāng)你年幼的時候,極力想掙脫她的懷抱,撲向外面的世界,卻被她粗糲的食物打磨出獨特的味蕾,被她淳樸的鄉(xiāng)音暈染出獨一無二的性格,在放飛幾十年之后,被老屋牽絆著,被村口的老槐樹召喚著,被門坡的那棵杏樹指引著,急切地?fù)湎蛩謧牡仉x開她,在遠(yuǎn)離她的地方用無數(shù)個夢來思念她。可當(dāng)你千里迢迢風(fēng)塵仆仆地回到老家時,只有蒼松翠柏中的親情,才能牽掛住你再也無處寄放的思念。
回老家,真是一件傷感的事情,也是每一個游子一生都走不出、走不完的心路。此時此刻,回望故鄉(xiāng),韓子厚的《零陵早春》縈繞心頭:問春從此去,幾日到秦原?憑寄還鄉(xiāng)夢,殷勤入故園。(金屬科技公司 王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