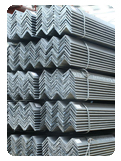昨晚又夢見老屋,恍惚中又遇見了老井。
老井離老屋很近,穿過一條窄窄的小巷,走到大道,向左拐50米,便是老井。老井旁有一棵大柳樹,長長的枝條彎腰下垂,像村里姑娘長長的秀發,隨風飄搖,每年的春天枝條返綠,綴滿小嫩芽,從星星點點到綠意盎然,一天賽似一天地長。每年這時,去井邊擔水的父親,常常會帶回一節柳條,用刀子截取手指般長的一截,做成柳笛,嗚嗚吹響,引得我們姐妹圍著父親歡呼雀躍。
圍著老井的是一處用鵝卵石和青石砌起的井臺,井上安放一架轆轤,石頭的底座,鐵質的轆轤,上面纏著繩索,繩索緊繞著轆轤,一圈挨著一圈,像個線軸,繩子的末端有一截鐵質的鏈扣。從井口向下望去,陰涼深邃,人影在井水倒映,無端地生出幾許涼意。記憶里,老井的周圍總是很忙碌也很熱鬧,每天早晨,扁擔上的鐵鏈碰著鐵桶的叮當聲、轆轤搖動的吱呀聲,嘩嘩的倒水聲,充盈在靜謐鄉村的上空。挑水的人們來來往往,古銅色的臉膛,精瘦有力的身板,黑色的、白色的粗布褂、千層底兒的黑布鞋,伸出粗大的手掌、有力的臂膀,熟稔地掛好水桶,順到井口,逆時針轉動轆轤。伴著吱吱呀呀的聲音,將水桶放到井里,等水桶到了水面,用力晃動繩子,將水桶壓到水面下,灌滿水桶,再順時針搖動轆轤,滋滋嘎嘎的響聲中,一桶清水順勢而上,探身、拉出來,轆轤順勢回放兩匝。如此反復,兩桶水灌滿,扁擔上肩,噠噠噠噠隨著沉穩的步履散向各家門戶。
看著大人挑水,我們這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也逞強好勝,挑了空桶去水井取水。記得第一次去挑水,父親很不放心地緊跟在我身后。初生牛犢不怕虎,我站在水井邊,毫無懼意。父親站在水井的一側,耐心地給我講步驟,系桶、放桶、打水,提桶,倒水。我簡單地認為沒什么難的。可真真作起來,那轆轤偏不聽話,卸下水桶時雖搖搖晃晃,倒也順利,等水桶到了水面上,任你薅著繩索,左搖右擺,卻無論如何不肯往水下走,運氣好的,會勉強打進半桶水,運氣不好的,水桶便從繩索脫落。最后,還是父親幫助我打好半桶水,可以往上提了,甩手一搖,才知道輕重,父親叮囑我小心,告訴我初學者被轆轤拐把打到的也時有發生,不由心生余悸,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氣,唯恐受傷,又怕被人恥笑。好不容易打好水,扁擔上肩,也走不了直線,父親跟在我的身后。水桶搖搖晃晃、人搖搖擺擺。顫顫巍巍過了門檻,恨不得馬上把水桶卸下,父親急忙接住水桶,將清水入缸。父親一邊心疼地拍拍我,一邊欣慰地說“閨女長大了!”而我拍拍雙手,仿佛力氣又來了,肩膀上的疼痛卻仍在,隔天終也忘記了。
水井邊的記憶總是混著鄉村俚語,水井旁的柳樹下,是洗衣服的好地方,也是家庭主婦的戰場,母親也常常在這里洗衣。大鋁盆,搓衣板,一家老小待洗的衣物放在荊條編成的籃子里,一桶清水合著轆轤的歡叫從老井中搖蕩而出,傾瀉到水盆中。嬸子、大娘、大嫂子一邊響亮地聊著,一邊麻利地把衣服放進盆里。
嘭嘭的棒槌聲,嚓嚓的搓洗聲,水桶叮叮咣咣的響動聲,井邊的熱鬧,直到傍晚才散去。
入夜后的老井,似乎也跟著小村進入了沉睡,靜靜的沒有一絲聲響,拐把轆轤也安靜了下來,井繩靜靜地懸垂著,一動不動。老井的上空,星星一眨一眨地閃著亮晶晶的眸子。老井的旁邊,忠實的老柳樹安靜地佇立著,將身影隱藏在月亮的清輝中。只有蛐蛐清脆悅耳的叫聲,唧唧吱——唧唧吱——,刺破夜的寧靜。
多年后,再次回到老家的時候,不經意間又看見了老井,昔年熱鬧的老井早已變了模樣,顯得孤寂落寞,只有一臺水泵為伴,只有送水的人光顧,老井似乎被大家遺忘了。可它依然敞開胸懷,源源不斷地將水送進各家各戶,滋養著小村一代又一代的兒女……
我望著老井,老井望著我,遠去的記憶忽然像風一般跑來,仿佛又看到年輕的父親挑著水桶,穩健前行;仿佛又看老柳樹下母親洗衣的身影,過往迅疾地拂過腦海……(漢鋼公司 江 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