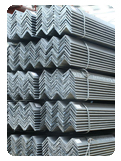相較于漢中初春的繁花似錦,關中大地的春天總是姍姍來遲。清明前后,枝頭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才開始散發淡淡的芬芳。然而,父親卻沒能目睹這春日盛景。
與父親上次相見不過兩個多月,我便接到他病危的消息。妥善安排好工作后,我即刻踏上從漢中前往大荔的動車。動車上,車窗外的田野、樹木飛速向后掠過,遠處的高樓由小變大,又轉瞬變小,可我卻覺得列車的行進速度比往日慢了許多。車廂內一片靜謐,我迫不及待地打開手機,翻看著與父親為數不多的照片,思緒不由自主地回溯到父親的一生,那些過往的回憶在腦海中久久縈繞,難以消散。
父親的一生,是操勞的一生。他出生于20世紀40年代一個貧困家庭,祖父母體弱多病,兄弟姐妹眾多,家庭經濟極為拮據。在我的記憶里,父親白天忙于教書育人,放學后還要匆匆趕回家中,協助母親照料年邁的祖父母、尚未成家的兄弟姐妹,以及年幼的三個子女。那時的父親,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,撐起了整個家庭的天空,任由山間的云霧自在飄蕩;又似一頭勤勞的黃牛,耕耘著麻陽村的每一寸土地,期盼著秋日的豐收;更如一座不朽的豐碑,銘刻著一代人勤勞樸實、默默奉獻、永不向困難低頭的精神品質。父親常對我說:“人勤快點,日子就有盼頭。”
“文革”結束后,父親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。1983年,他所帶班級有兩名學生被復旦大學錄取,在全縣引起了不小的轟動。我至今仍清晰記得,他當時喜形于色的模樣。為了鐘愛的教育事業,父親櫛風沐雨、奔波勞碌,終因積勞成疾,本該含飴弄孫、安享晚年之時,卻被多種疾病纏身,前幾年更是臥病在床。即便如此,父親躺在病榻上,仍驕傲地對我說,他這一生在教育事業上盡職盡責、不辱使命,為教育事業殫精竭慮、大膽創新,這些經歷就是他人生最寶貴的財富。受父親的影響,我們將父親的精神轉化為家庭的精神財富,形成了良好的家風。
懷著急切與期盼的心情,我輾轉回到數月未見的合陽縣甘井鎮麻陽村。此時,村莊籠罩在陰云之下,仿佛烏云稍一壓低,天空便會落下淚來。與年初離開村莊前往漢中工作時的戀戀不舍相比,此刻我的腳步沉重得仿佛能踏碎腳下的水泥路。站在大門口的哥哥見我歸來,立刻將我帶到父親床前。此時的父親已無法言語,只能用失去光澤的雙眼凝視著我,我無從知曉,他是在責怪我放下工作趕回來,還是因在這一刻見到我而感到滿足。
當天夜里,父親與世長辭,結束了他79年短暫而光輝的生命歷程。那一夜,天色漆黑,整個院子只有我站立的地方燈火通明;那一夜,寒風凜冽,即便身著厚厚的棉衣,也難以抵御刺骨的寒冷;那一夜,我徹夜未眠,與父親相處的點點滴滴,在腦海中拼湊成一幅幅鮮活的畫面。
經過幾天的忙碌奔喪,又到了返回漢中的日子。走在麻陽村熟悉的鄉間水泥路上,我的腦海中浮現出父親與母親、姑姑、妻子、哥哥、兒子等親人在此散步的場景。迎著光,父親佝僂著腰,顫顫巍巍地拄著拐杖,曾經寬闊的臂膀變得消瘦,花白的頭發格外醒目。他像當年站在講臺上一樣,講述著年輕時的故事,只是少了往日的意氣風發,只留下一道長長的背影,投射在水泥路上。
前些日子,我打電話告訴哥哥,清明時會回去看望母親,并為父親掃墓。哥哥卻說,他會悉心照顧好年邁的母親,讓我銘記父親恪盡職守、兢兢業業的精神品質與良好家風,堅守好自己的崗位,他會帶著侄子去祭奠父親。
不知不覺,已過去一月有余,清明已至,關中大地生機勃勃,花香四溢,春柳搖曳,渭水潺潺流淌,春燕在屋檐下尋覓著筑巢的材料,萬物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。唯獨父親拖著疲憊一生的身影,遠去另一個世界。這一去,或許是孤寂,或許是新生,但對我而言,這一去意味著訣別,意味著永遠的分離。(漢鋼公司 王德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