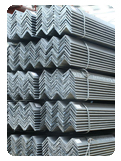陜北的秋來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秋風吹一陣,陜北便冷一分,清晨的秋風裹雜了初冬的寒意,山峁上的杏樹、山桃樹、蘋果樹的葉子經不起秋風的肆虐,無奈地隨風飄搖起來。喜鵲搭在白楊樹上的窩又露出原本的模樣,棗樹上成群結隊的麻雀瞅著院子里沒人,箭一樣馳向院子里放的雞食槽,狠狠啄幾口,轉眼又飛回到了棗樹上。
陜北的黃土很厚,厚的能承載起千萬年來這里人們的繁衍生息,何況是裹著黃綠色的軍大衣,蹲在地畔上抽著旱煙鍋的父親,和三五結隊在溝坡峁坬上往來啃著枯草的羊群。陜北的黃土地很是廣袤,一座山連著一座山,一層疊著一層,就像父親放的山羊身上的絨毛,一絲連著一絲,一層籠著一層,不知不覺擋住了凜冽的寒風。一個人,一群羊,不遠處的窯洞上冒出來又立即隨風而逝的炊煙,讓城隍梁這個小村莊顯得有些孤寂,但父親對生活的熱愛從未消減。
父親的羊群在陜北并不算起眼。羊在陜北農村最容易見到,且最容易飼養,買一只種羊和幾只母羊,幾年的工夫就會變成一群羊,只要攔羊人喂養得好,羊羔長著也快,頭一年的羊羔子,第二年就能下崽,我清楚記得,前些年父親買了四五十只羊,三四年的時間,已然成了一百多只,期間還賣了幾十只,以至于在榆林和延安一帶,無論走到哪個村莊,都能見到成片的羊群。
為了羊群,父親投入了太多的精力。每年秋收時分,半夜三點鐘父親就帶著母親到腦畔后的玉米地開始掰玉米,二三十畝的玉米也要行動個早,不然等下雪了,玉米秸稈就會被浸濕,這些秸稈就是羊群整個冬天的草料,丟棄不得。父親和母親戴上頭燈,母親在前面掰玉米棒子,父親在后面砍玉米秸稈,黑寂的夜晚,除了風聲,就是父親和母親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和砍玉米秸稈的“沙沙”聲了,公雞打鳴,山與天交匯的地方只露出一絲魚肚白時,玉米已經砍倒了一片。有趣的是,院子里的雞這時也來湊熱鬧,挺著胸膛,邁著驕傲的步子跟在父親后面溜達起來,仔細尋找玉米上掉下來的蟲子。
太陽跳出山頭,拱了拱憋屈的身子才放出金黃的光芒,父親催促母親趕緊回家做飯,自己再趕著趟兒砍一些。飯后,母親又回到玉米地里掰玉米,而此時父親扛起攔羊鏟子,披上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軍大衣,到羊圈把大羊和羊羔分開,把大羊群順著澗畔峁子下的小路趕向溝旮旯去了。父親放的羊很通人性,頭羊走得太快,父親抄起鏟子扔塊土疙瘩,羊群瞬時就慢了下來,當羊爬上地畔靠近莊稼地時,父親再抄起鏟子扔塊土疙瘩,羊群又會重新回到溝坬地吃草。傍晚,太陽快要落下時,不用父親催促,羊群在頭羊的帶領下,邊吃草邊悠然自得地向羊圈走去。
曾經父親是靠販賣糧食支撐起了這個家,隨著父親年紀越來越大,已搬不動沉重的糧食,便和母親回到了城隍梁老家,過上了養羊種地的生活,把整個家也擱在了羊背上。每年種的二三十畝玉米,父親并沒有賣掉,而是全部拿來喂羊,玉米顆粒是飼料,秸稈就是草。羊也沒有辜負父親的希望,每年陽春三月,把羊身上剪下來的絨毛賣掉,隨隨便便也是萬把塊錢,除去種地的化肥種子還有不少剩余,每年過節賣掉的大羊又是一筆收入,可以說,父親和他的羊群托起了整個家。
我因為在漢中工作,留在陜北城隍梁這個小村莊的日子屈指可數。也是前些天趁著國慶節回了一趟陜北,與母親在地里掰了些玉米,和父親在山溝旮旯里放了幾次羊,我的心再一次留在了陜北……
哪怕是回到漢中,我隔著千山萬水仿佛再一次看到了母親放下手中的玉米,拿著小頭給羊羔砍苜蓿草。父親在澗畔底的溝旮旯里,時不時罵兩句不聽話的羊,時不時對著羊吼幾句地道的陜北民歌。(王德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