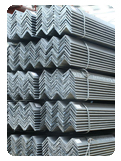秋剛過,滿眼色彩像被馬良的神筆抹過,蔥蔥的綠一夜之間焦黃了。

看那路旁遮擋視線、阻礙眺望的法桐,沒有了厚實的冠,輕薄泛黃的葉子,蹊蹺地垂吊在粗枝細稈上。凝結(jié)成低溫的風(fēng),也不打擾眼前凝望的風(fēng)景,任憑刺向空中的花去,粗糙骨感地展示著枯枝的文化,把一種獨有的美掛在天地間。
落沒了石榴的樹,還想著新一輪孕育,幾顆花萼挺著,孤單地攀著已經(jīng)坐化了的果實,秋吐出晨露,溜出最后一朝嵐靄,石榴樹也在戾風(fēng)中凌亂;它胡亂地撒著葉子,扭動著纖細枝條,甚至跟不上節(jié)奏地搖擺,搞得冬只好淺淺地凍,淺淺地寒。

瘦柳纖枝,嫩煙輕染,挺在秋里還細葉如刀,飛剪著一季盎然繁華,可初冬降臨,輕葉不堪冷云壓,疏疏一樹五更寒,醞釀至半截的夢想,也就隨風(fēng)蕩落,只留下半禿的樹,挺著脊梁,低著頭,不卑不亢地哼著“從頭再來”。
悄悄潛入日月里的初冬,認真履行著“美麗凍人”的職責(zé),只是林木不舍春,覺得紅花未盡妍,綠抹未央罷了;有果無果的樹,葉子黃了落,陸續(xù)黃陸續(xù)落,偶爾有一兩顆果子,端端地坐在樹梢思考,所有的心思,隨著葉子兄弟無端的飄零,都化作來年的期盼、今年的眷戀。
弄了一頭黃葉的春樹,正哼著秋天的歌,原以為舞弄秋風(fēng)立潮頭的驕子,能把壯美的錦旗扛到春,哪知,初冬的雨剛過,春樹便急切的眠睡去了,抖掉黃葉不算,枝枝芊芊也摔到一邊,光著身子走,不到春天叫醒,絕不會伸出手來回應(yīng)。
常綠的樹,沒有那么多性格,四季就一個態(tài)度——死板的綠。然而今冬不同,有些常綠的色,羞澀的漸變,有褐又黃,但卻不肯低頭落地,或許它是一種提示,或許本身就堅硬;或許初冬就是這種風(fēng)景,綠不繁盛,錦黃一片,頹廢中有驚詫,飄零中有不甘,各種姿態(tài)戀春,赤裸裸地把自然的美展現(xiàn)。初冬,宛如一首悠揚的詩篇,每個細節(jié)都流淌著歲月的華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