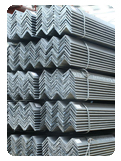清明假期,我和姐姐回到了榆林老家上墳。四月的黃土高坡依舊荒涼,溝壑縱橫的山峁上,風卷著細碎的沙土,掠過枯黃的草莖。除了村里又少了幾張熟悉的面孔,一切似乎都沒什么變化,山還是那樣沉默,窯洞還是那樣低矮。
記得初中時初讀艾青的《我愛這土地》,老師逐句講解,說這詩里飽含對故土的深情。可那時的我,坐在教室里,望著窗外灰蒙蒙的天,只覺得詩句遙遠,不過是考試要背的段落罷了。如今,當我再次踏上這片養育我的土地,站在祖輩長眠的山坡上時,那些詩句才突然有了重量,它們不再是紙上的鉛字,而是從黃土地的裂縫里滲出的嘆息。
風與墳
陜北的風,總是帶著一股倔強勁兒。它從遠處的山梁上撲下來,卷著沙粒,抽打在臉上,生疼。小時候討厭這風,覺得它粗糲、蠻橫,吹得人睜不開眼。可如今回來,卻發覺這風里裹挾著某種熟悉的氣息,干燥的黃土味、燒秸稈的煙味,還有不知名的野草在風里折斷的苦澀。
我跪在父親的墳前,沉默不語,只是低著頭慢慢的燒著紙,忽然想起小時候父親也是這樣,在清明時帶著我們上墳。那時覺得上墳不過是例行公事,磕頭、燒紙、填土,然后匆匆回家。可如今才明白,這一鍬一鍬的土,不僅僅是修葺墳塋,更是一種無言的承諾,告訴逝去的人,這片土地,還有人記得。
荒涼與生機
黃土高原的四月,荒涼仍是主調。山峁上的草還未返青,枯黃的莖稈在風里搖晃,像是大地伸出的干瘦手指。可若細看,荒涼之下,其實藏著微弱的生機——田埂邊冒出的薺菜嫩芽,石縫里鉆出的蒲公英,還有那些不知名的小野花,星星點點地綴在黃土上。“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?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”從前不懂,為何有人會對這樣貧瘠的土地懷有深情。可當我蹲下身,手指觸到干燥的土壤時,忽然明白,這片土地的貧瘠,恰恰是它最真實的面貌。它不偽裝豐饒,不掩飾苦難,只是沉默地承載著一代代人的生與死、離與歸。
離去與歸來
村里的人越來越少了。年輕人都去了城里,留下的多是老人。路過兒時玩耍的打谷場,如今已長滿荒草。曾經的鄰居見到我,瞇著眼認了半天才叫出我的小名,而我只能尷尬的笑笑,只能小心翼翼的叫一聲啊姨,是啊,我離開太久了,久到連故鄉的人都變得陌生。
可這片土地似乎并不介意我的疏離。它依舊以同樣的姿態迎接我,風還是那樣刮,山還是那樣靜。我突然意識到,無論我走多遠,這里始終有一個坐標,標記著我的來處。就像那些墳塋,無論后人是否年年祭掃,它們都靜靜地立在那兒,成為血脈里的烙印。
羽毛腐爛在土地里
我望著跳動的火焰,想起艾青那句:“然后我死了,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。”從前覺得這句子悲壯,現在卻覺得它溫暖。羽毛腐爛在土地里,不是消亡,而是另一種存在方式,就像祖輩的骨血融進黃土,化作春草;就像我們的記憶滲入溝壑,成為風中的低語。這片土地不擅言辭,但它記得所有在這里活過的人。燒紙的灰燼被風卷起,打著旋兒飄向遠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