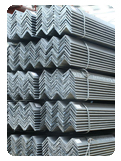老張說:“如果當年自己留在部隊,那一切都會不一樣……”
至于怎么個不一樣法,老張沒有說。沒有說并非他不愿意說,而是因為5年前腦卒中留下了后遺癥。老張的語言功能受到了影響,很多東西想表達,卻無法很好表達。
老張沒有說出的后半句,潛藏著的是一個“孔融讓梨”般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寫滿了一個年輕人的至善與遺憾,也伏筆了他坎坷不易的一生。
1976年,老張當時還是小張,正在某部隊服役。本該他提干的當口,因不忍比自己年長的戰友退役,故而將名額讓了出去。只是晚一年提干,沒什么大不了的。小張心里這么想著。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,政策發生了變化,小張提干無果,即將面臨退役回鄉。
領導寬慰他,暫且多留一年時間,也許事情還有轉機。但小張執拗:政策已然宣布了,還能有什么轉機?繼續死皮賴臉地留下,那是給部隊和領導添麻煩。況且回鄉也并非就是壞事,毛主席說了,廣闊天地,大有可為。
小張懷著一絲遺憾離開部隊回了家,與其他人一樣相親、結婚,并滿懷信心地開啟了自己的農民生涯。
剛回鄉那幾年,小張干勁十足。每日天不亮就出門上工,伴著星光才疲憊地往回走,月月滿勤全工分,甚至還因為表現優異當上了生產隊的隊長。
時間來到80年代,小張的心開始起了變化。雖然靠著土地能夠吃飽穿暖,但精神上總是覺得少了點什么。日復一日面朝黃土背朝天,自己收獲的是什么?
小張想去城里開店,他想憑借自己在部隊學習的技能在城里立足。
然而身為村支書的父親卻不同意小張去城里,一來覺得那是瞎折騰,二來私心里想留住這個最愛的兒子在身邊,好將一身木匠手藝傳承下去。
小張不喜歡做木匠,因為不喜歡做木匠,所以在高中畢業后選擇了去當兵。如今即使回到了村里,他依然不喜歡做木匠,日復一日圍著木頭和鋸子、刨子轉,和在土地上刨糧食,沒有什么分別。
最終,小張因為孝順沒有違逆父母的意愿去城里開店,卻也沒有像父親希望的那樣傳承木工手藝。他依然每日辛勤地勞作,眼睛里卻少了些許神采。
再后來孩子們出生。再后來父母相繼離世。小張也終于不再年輕,不再想去城里開店的事。
為了生計,為了支付幾個孩子上學的學費,為了孩子們不再窩在小鄉村里消磨歲月,他撿起自己在部隊上學會的廚藝,開始承接村里的紅白喜事席面,稱謂也正式變成了老張。
老張也曾遠近聞名。方圓幾十公里,紅白喜事找他做席面的人不在少數。但是每次做完席面回到家里,老張一身疲憊,除了蒸饃就蔥,他什么都吃不下。這成了親鄰打趣他的一個笑談,說他不會享福。
其實,哪有不會享福的人,只是沒有遇到享福的命運。
孩子們一個接一個長大、上學,盡管經濟負擔很重,但老張從未動過讓哪個孩子停學出去打工的心思。他期盼著孩子們能考上大學,走出去,彌補自己曾經無緣大學的遺憾。
如老張所愿,孩子們考上了大學,也走出了鄉村。本想著終于能夠松口氣了,老伴卻又不幸患了重病。除了大女兒在身邊偶爾能幫忙照顧,其他孩子要么離得遠、要么還在上學,沒辦法指望。老張一個人艱難地扛下了所有責任,雙鬢白發驟增。
老伴離世后,老張孤孤寂寂地過了三年。因為家里有地要種,有屋要守,他不愿離開村里去城里生活。孩子們心疼他一個人,擔心他的身體,于是勸說他如果有合適的人選可以考慮再找個老伴。
后來經人介紹,老張找了一個與以前老伴同名的人,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種注定。
新老伴心地善良,只是性格潑辣強勢一些。她不介意老張家境貧寒,還有兒子尚未娶親。在她的觀念里,只要手腳能動,就不愁生活過不好。
她支撐起老張的半邊天,與他農忙時一起下地干活,農閑時經營鄉村農家樂。眼看著日子一天好過一天,老張卻倒下了。突發腦卒中,老張躺在了病床上,一度失語不能言,腿部無力不能行。
老伴不離不棄地悉心照顧老張,督促他運動,陪他說話,讓他能夠清晰表達自己不至于急躁,能夠慢慢自由行走,不至于下半生在輪椅上度過。
生病以后的老張變得喜歡回憶從前。他想起自己在外公家度過的無憂無慮的童年,想起求學時期自己也曾壯志滿懷,也憶起當兵時因為謙讓而錯失的良機……
如若一切能夠重來,老張會不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?他的一生,會不會變得不一樣?
也許是會不一樣吧!但是后來又轉念一想,只要這世界還是客觀的世界,不存在帶著前世記憶重生這件事,老張就依然還是老張。他依然會選擇將機會讓給戰友,依然會堅持“父母在,不遠游”的古訓,依然會鼓勵孩子們求學上進,依然會無微不至地照顧生病的老伴,依然勤勤懇懇、平平凡凡地過完這一生……
因為老張說過,這一輩子,他就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、一個講究信用的人、一個遵循傳統的人、一個孝敬父母的人。
老張沒有說,他其實還是一個不會說話、卻把心底的溫暖與關愛表現在行動上的人。(龍鋼公司 趙菲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