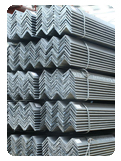前幾天,遠在山東淄博的同歲堂弟,在朋友發了一組蝸牛的照片,不由得將我的記憶拉回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個鄉村小學,那個校門前的照壁前,有一棵盛開的木槿,里邊有好多好多的蝸牛,到處爬著,就是這個地方,一個讓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地方。
我們那個自然村,處在三縣、兩個地區交界的特殊位置,北邊是喬山延綿的土坡,東邊是漆水河沖積出來的河槽,別看是連畔種地,各縣口音就會有差別。盡管民間互通有無,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套親戚,但是由于行政劃分的緣故,官方來往不多。在這種大背景下,我們這個自然村就有了自己獨立的村部,獨立的小學就應運而生,在這所不起眼的鄉村小學里,承載我童年的無限歡樂。
學校不大,五個年級齊全,三間教室,兩棵不知道多少歲的歪脖子土槐樹,復式班教學(就是一、二年級在一個教室,三四年級在一個教室,五年級一個教室),老師一般先是給高年級上課,低年級同學可以跟著聽講,完了高年級同學做作業自習,老師才給低年級同學上課,這種復試教育,要求老師是全才,學生聽話。可一旦上起課來,就不是那么回事,一般都是低年級同學調皮搗蛋,一會上廁所,一會又吵起來,老師不得不停下來斷官司,紅脖子漲臉的一轉身,又會嘻嘻哈哈的扭作一團,好得跟一個人一樣。這樣的教學方式對老師要求很高,語文數學音樂美術樣樣都能拿得起。這樣的教學方式,偶爾會發現幾個天才,低年級的學生學會了高年級的課程,小學五年連跳,三年就小學畢業了。快樂的回憶總是笑意盈盈,說說最有趣一件事:那時我剛上小學,老師也是高中剛畢業,喂了半年生產隊的“老黑”,就被拉過來當我們的班主任,第一次讓我們排隊,同學們都亂作一團,老師氣得哭笑不得:你們連我養的小豬都不如,那些豬我一吹哨子,都整整齊齊地排成一排,等著我給它們喂食,比你們強多了!這個經典段子流傳了許多年,現在那個老師已經退休多年,但是每次見面,大家都讓老師吹哨子,笑作一團。諸如此類的快樂比比皆是:用橡皮筋打蒼蠅,用木桿阻斷螞蟻回家的路,捉土槐樹上的吊線蟲放到鼻子上,把椿樹上的“花大姐”綁在女孩辮子上,給課桌中間釘釘子劃“三八線”,用老柏樹的樹皮點燈等等,過去的那一幕幕,隨著年齡的增長,感覺越來越有趣,回味綿長。還有愛打人的王校長,感覺好老,中山裝整整齊齊,整天板著個臉,記得教我們珠算,我對珠算無感覺,上課老是看窗外嘰嘰喳喳的麻雀,老校長的算盤,有一天摔倒我的課桌上,算盤散了架,珠子在教室里蹦蹦跳跳,我嚇得好幾天都沒敢上學,盡管我最后一直很努力地學習珠算,但是到現在還是一腦子漿糊,拎不清三下五除二。大陳老師高高大大,儀表堂堂,總是走在校園的磚墁路上仰著頭,張著嘴,每每走過十幾步,一個噴嚏才能在他的眼淚里噴出。老王老師和藹可親,是語文老師,特喜歡我這個愛寫作文的小孩,他總是摸著我的頭說,多看書,書會告訴你很多你不知道的東西,讓你以后走得更遠。還有小王老師,是個教數學的,他家不是我們村上的,他自己做飯,他總是利用做飯的時間,叫我去他的灶房,給他燒火,他邊做飯,邊給我講題。正因為有這些可親可敬的老師,我們那一年小學畢業升學考試,平均成績名列全鎮前茅,一個不起眼的小學,萬眾矚目。小學的條件很簡陋,一、二年級沒有木制的課桌板凳,用水泥板當做桌面,用磚頭壘砌支撐起來。這樣的課桌夏天還好,趴在上面涼涼的,蠻舒服,可是到了冬天,涼氣浸透棉衣,直竄心窩。小時候的冬天很冷,基本零下十攝氏度左右,整個冬天北風凜冽,白雪皚皚。沒有暖氣,沒有爐子,甚至窗戶上的玻璃打了,用報紙糊上,全是洞,北風吹得呼啦啦地響,小孩子一個個凍得縮頭縮腦,下課了,就在朝陽的土墻邊“擠暖暖”,一下子就會渾身暖和起來,笑聲震落老槐樹上的積雪。校園最愜意的日子就是夏天,老師有時候就把課堂搬到老槐樹樹蔭里,老師給在老槐樹上掛個小黑板,小孩子根本就不用課桌凳子,在光滑平整的土地上,每個人畫一個方框,用廢電池的石墨棒在地上寫字做題,老師轉來轉去檢查,隨時踢你一腳,用腳指點你更正錯誤。現在回想起來,此做法真的是低碳環保,親近自然。
記憶最深的,現在想起來最爛漫的事,是在學校門口的照壁前有一棵不知道多少歲的木槿花,在那時幼小的心里,感覺它很大很繁茂,總是開著無數紫色的花,粉粉的。底下總是濕漉漉,蝸牛們自由地爬來爬去,我老是想不通,他們忙忙碌碌地爬來爬去,是在干什么?它們吃什么東西?它們晚上在哪里睡覺?誰跟誰是朋友?老師說這個小孩有思想,他們也解答不了我這么多的為什么,同學們都笑我是個傻子。我那時幼小的心靈里,就種下思考的種子,隨著年齡的增長,生根發芽,伴我走出那個不起眼的小村莊,走向更遠的天際線。每每夜深人靜的時候,回想起那個小學校,那些敬愛的老師和可愛的自己,不由得會心一笑,拋棄所有負能量,平復一下心情,又一次輕裝上陣,迎著每天初升的朝陽,微笑著生活、學習和工作。(寶銅聯合黨委 王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