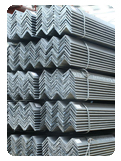母親常說,吃不窮穿不窮,計劃不周要受窮。母親是個農民,她堅信只要自己有雙肯勞動的手,再苦的日子也會挺過,也會有發生變化的那一天。長期以來,支撐她信念的是那一件件被她視為珍寶的農具和日常器物。
母親一輩子在田頭山野間忙碌,與她形影不離的伙伴是一頂斗笠、一只背籃和一把镢頭。背籃是母親跟著別人學習用竹篾編的,用來背蔬菜、背柴火、背豬草,一年到頭幾乎不離背。镢頭是田間勞作的主要工具,镢頭把油光锃亮,握在手中很溫潤,很趁手。斗笠是母親用來遮陽的,頭頂太陽高懸也能遮一遮,留一點陰涼在心里。
母親喜歡置辦器物,對器物格外愛惜,輕易不會扔掉。
在農家,簸箕、扁擔、籮筐、曬泊子……少一件都不方便。母親總是置辦得齊整,隨用隨拿。母親有點看不慣鄰居霞嬸,霞嬸每次趕場回來總是買肉,買水果,一家人總在“嘴上”弄事情,而柴刀、鍋勺之類的常用工具舍不得買,總是到左鄰右舍借來借去。但村里人誰家辦紅白喜事,借桌子、借碗,母親卻很樂意。她認為這是人生的大事,也用不了幾回,大家應該相互幫襯,舍得把她多年不用的珍藏借出去。
小時候,巷子里總有上門收廢品的,隔壁的霞嬸總能在家里找到廢書、爛鍋破布去換難得一見的糖果。我很羨慕,于是也在家里四處翻找,母親卻制止了我:“家里的東西樣樣有用,沒有廢品。”我將信將疑,一邊用山里挖的白蒿、防風、柴胡換取些零花錢,一邊時刻操心著家里出現的廢品。一天早晨,正在刷鍋的母親“呀”了一聲,連忙把水倒了,舉起鍋逆著光瞧,黑黑的鍋里透出一個亮點,鍋底破了。我高興地說:“媽,鐵鍋爛了,這次可以當破爛賣了吧。”這鍋起碼有三斤,五分錢一斤的廢鐵,這可是一筆大的收入。“給你當破爛賣,太浪費了,哪天補鍋師傅來了,釘個巴釘就行了,你不許打鍋的主意啊。”母親說著,把鍋擦干凈,用報紙包了放在案板下。沒過幾天,那個補鍋的師傅還真的來了。母親拿出鍋,補鍋師傅拿出專門的工具,順著鍋裂開的口子敲敲打打,裹上黃泥,釘上一個鍋釘,就這樣母親花一塊錢把鍋給補好,這鍋又用了很多年。
有一年,家里買了一把黑布傘,十多年過去了,我自己上學用的傘不知換了多少把,但母親的那把黑布傘還在用,只是傘面換了好幾次,傘骨依然完好。
前些年,回老家看望母親時,總是一大把塑料袋吊在手上,母親見我每次來都是如此,便問我道:“怎么不準備一個竹籃子買菜?”我回應道:“現在買一根蔥,人家都會給你一個塑料袋,輕巧方便,誰還需要竹籃子?”
隔天早晨,我發現廚房里竟然有了一只小布袋,精致小巧,還繡有一朵小花。我欣喜地提著小布袋去買菜,仿佛回到了童年時光,有一種回歸自然的喜悅。青椒、豆角、西紅柿、黃瓜,一樣一樣放進布袋里,覺得日子踏實而美好。回家把菜整理好后,母親把布袋洗得干干凈凈晾在衣架上,準備下次再用。
“器物前半生是創作者賦予的……后半生則拜托給了選擇它的人。”被母親選到身邊的每件器物都是母親的好伙伴,都能得到母親的珍愛。镢頭、鐵锨、拿進家門之前一定要把泥土擦干凈;簸箕、籮筐不能直接擺放在地上,要懸掛起來;斗笠要掛在墻壁上,雨傘晾干后折疊好要用袋子扎好;待客用的茶杯、碗筷等擦干凈水漬,曬干收在柜子里,有客人來才用;蒸饃的籠圈,打豆腐的匣子,用完要清洗得一點殘渣都不能留,否則就會有老鼠來咬……
母親的節儉,是居家過日子的樸素,是對生活的執著與耐心,是對生活的一份珍惜,更是一種情懷。(龍鋼公司 薛萬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