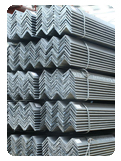母親的手,向來是粗糙的。指節突出,皮膚上爬滿了細碎的皺紋,像是干涸的河床上龜裂的泥土。指甲修得極短,邊緣總有些細小的裂痕,顯出一種勞作過度的疲憊。這雙手,捏過針線,揉過面團,搓過衣裳,也擦過我的眼淚。
我幼時多病,每每發燒,便見這雙手在眼前晃動。先是冰涼的掌心貼上額頭,接著便是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響——母親在擰濕毛巾。她將毛巾疊成長條,敷在我的前額,動作很輕,卻又極穩當。毛巾熱了,她就翻個面;再熱了,便又浸了冷水重新擰過。如此反復,直到我的高熱退去。半夜醒來,常見她倚在床邊打盹,手里還攥著半濕的毛巾。
母親的手很巧。家里經濟拮據,我的衣服多是鄰家孩子穿剩的。母親便用這雙手,將舊衣拆了,翻個面重新縫制。有時還在磨損處繡個卡通圖案,或是釘個布貼,竟比新衣還要別致。線頭在她指間穿梭,針尖偶爾擦過頂針,發出細微的"叮"聲。我趴在一旁看,她便笑:"男孩子家,看著干啥。"那枚頂針至今仍躺在她的針線盒里,光澤暗淡。
廚房是母親的另一處戰場。她揉面的樣子極是好看。面粉倒在案板上,中間挖個坑,倒水,然后便用手指慢慢攪動。漸漸地,散亂的面粉聚攏成團,她的手也由白變黃,沾滿了黏糊的面渣。揉面要用力,我看見她的小臂肌肉繃緊,額角滲出細汗。面團在她掌下變形、伸展、折疊,最后變得光滑柔韌。蒸出來的饅頭,白胖松軟,帶著微微的甜香。我貪嘴,常趁熱撕著吃,她便用沾著面粉的手點我額頭:“饞貓”。
洗衣是樁苦差事。那時尚無洗衣機,母親便在院里的水泥池邊搓洗。寒冬臘月,水冷刺骨,她的手浸得通紅,關節處裂開細小的口子。她抹些蛤蜊油,繼續搓。衣服在搓板上發出"咯吱咯吱"的聲響,泡沫濺到圍裙上,很快結成冰碴。我幫她晾衣服,竹竿太高,她就把我舉起來。我聞到她頭發上的肥皂味,混合著手上的凍瘡藥膏氣息,莫名安心。
我離家讀書那日,母親在月臺上替我整理衣領。火車鳴笛時,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塞過來一個布包。車開了,我打開看,是五個煮雞蛋和兩百塊錢。雞蛋溫熱的,想是她一直攥在手里。我回頭望,她還站在原地,雙手交疊放在身前,越來越小,終于消失在鐵軌盡頭。
五一回家,發現母親的手抖得厲害。她端茶時,杯蓋與杯身相碰,叮叮當當響個不停。我要接,她卻不讓:“別小看你媽”。她依然堅持自己縫扣子,只是線常穿不進針眼。我假裝看書,余光瞥見她偷偷用舌頭舔線頭,試了七八次才成功。
前些天視頻通話,母親興奮地向我展示新學的智能手機操作。她的臉擠滿屏幕,手指在鏡頭前笨拙地劃動:“你看,這樣就能看到你發的照片了”。她笑得像個孩子,可我的手卻無端發顫——那雙手上,老年斑已經悄悄爬上了手背。
母親的手,從豐潤到枯瘦,從靈活到顫抖,仿佛把一生的光陰都攥在了掌心里。那些皺紋深處,藏著我童年的溫度,藏著她說不出口的愛。如今我也有了孩子,才懂得,所謂母愛,不過是將自己的歲月,一寸寸揉進了兒女的生命里。(漢鋼公司 郭超鋒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