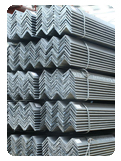在溝壑縱深的陜北,矗立在延綿起伏的黃土塬上的劉家園子,只是個不起眼的小村莊。這里沒有高樓大廈,沒有寬闊的柏油馬路,也沒有城市里人來人往的喧鬧,只有幾戶人家,幾處院落。悄悄地,夏日來了,村里村外除了樹上“知了知了”的鳴叫聲,這個蝸居在黃土高原的小村莊倒也顯得祥和。
村頭前的黃土塬畔上,一條幾乎是懸掛著的容得下勒嘞車的土路,此時長滿了雜草,卻依稀地能看到當年村里人,每天都要趕上毛驢,到溝旮旯的老水井馱水的痕跡。陜北缺水,村子里更加缺水,除了在下雨天能收集些雨水,用來澆菜地和飲牲口外,洗衣做飯的水,都要村民趕著驢或騾子,去五六里路以外,塬下的溝旮旯里馱上來。

母親要在家里做飯,馱水就只能靠父親了。天才微微亮時,我第一次跟著父親去溝旮旯里馱水,父親先給驢被好鞍子,而后兩只手用力將馱舉起,輕輕放在驢背上的鞍子間,再把倒桶掛在馱上,趕起毛驢向著溝旮旯出發,順手抄起一把鐵锨扛在肩上。我家的毛驢向來算溫順,不需要人牽著,也識得去溝旮旯老水井的路,順著土路一直走,我跟在毛驢后面,父親走在最后。路上遇到落下來的土疙瘩,父親會順手鏟起扔到溝里,有被雨水沖壞的渠廊,父親會在崖上鏟幾鐵锨泥土墊好。等到了溝旮旯的老水井旁,天已經大亮了,抬頭遠看黃土塬畔,還能看到金色的晨光也打在了塬畔上,甚是好看。
老水井有兩個水倉,是在兩山相交的紅砂巖石壁上挖出來的。兩口水倉都是高于地面一尺有余,向巖體內掘進三尺多,最后垂直向下挖掘四尺左右的方形水窖。水倉里的水清澈見底,底散落著兩塊雞蛋大小的石塊,都能分辨出哪里缺了棱角,頂上滲出的水珠“滴答滴答”地不停往下滴,在這小小的水倉里,泛起小小的漣漪。
父親取下倒桶,舀起半倒桶水等在嘴邊,“咕嚕咕嚕”猛灌了幾口,然后笑瞇瞇地說:“咱們這井水就是清涼甘甜,比城里賣的水還好喝。”說罷開始用倒桶給馱馱裝水。只見他緊握桶的木柄,伸入水中后再迅速提起來,就這樣左邊一倒桶,右邊一倒桶,各灌了十多下把馱馱灌滿后,把驢拉著轉個方向,在驢屁股上拍了一巴掌,驢便沿著來時的路,緩緩地朝著家的方向走去。父親拿起鐵锨,迅速把水井旁驢的糞便、小石塊、柴草渣子清理一番后,扛起鐵锨領著肩上掛著倒桶的我去追驢的腳步。
我甚是好奇這溝旮旯里,是誰開鑿了這兩口水井。父親告訴我,在他還小的時候,村里馱水是在更遠一些的小河,河水也很清澈,然而路途甚遠,若是遇到下雨天,河水變得渾濁不堪,三兩日也變不得清澈,很長一段時間里,人們都是把渾濁的水馱回來,等澄清了才倒進水缸里。后來爺爺當生產隊隊長時,帶著村里人尋找水的源頭找到這里,在與村民商量過后,便開鑿了這兩口水井,于是,用了近一年的時間,開了路,挖了井。這水井不僅離村子近,水量也足,自此,村里人有了固定的馱水點,哪怕還是用驢馱,也比從前少了不少工夫。
父親的解疑讓我瞬間明白,為何他每天馱水時總要扛上一把鐵锨了。父親告誡我不要忘記這老水井,以及當年挖井取水的人。父親說:“我老了以后,你還要來這里馱水,你的兒子將來也要來這里馱水,這水井就是咱們生活的根。”父親沒想到,隨著日子越來越好,幾年后村里就打了一口機井,村里人都壓上了自來水,結束了祖祖輩輩靠驢馱水生活的日子,我也走出了小村莊,到外面的世界工作、生活。
從父親把家搬到鎮上,再到我參加工作,我也曾多次回到黃土塬上的小村莊,站在塬畔上,看到了那條馱水的路,卻沒有看到馱水的人,也沒得空去溝旮旯里看看印在我腦海里的老水井。這時的我突然明白,當年父親讓我記住的其實不是老水井,而是老一輩人艱苦奮斗、飲水思源、敢于爭先的優良傳統。
去年夏天,我又回了一趟闊別已久的小村莊,看到了馱水的路滿是雜草,卻依舊留有當年村民趕著毛驢馱水的痕跡。在夏日的晨光中,我凝望著這條灌水路,仿佛看到了迎面走來了馱水的人,有一頭馱著水的毛驢,肩上掛著倒桶的孩子,后面還有扛著鐵锨的莊稼漢子,晨光灑在他們的臉上,映著額頭上滲出的汗珠晶瑩剔透,他們帶著希望走向美好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