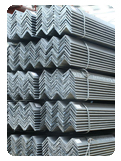小區(qū)門口,常有三輪車馱著玻璃罩叫賣“饸饹”的,這時,舌頭下面就像含了梅子,走近一看,不是蕎麥面的就是麥子面的,問人家是否有包谷面饸饹,小老板還不耐煩地嘟囔,意思是,苦澀的日子還沒過夠?那玩意有啥吃的,怎比這蕎麥有營養(yǎng)。
是的,現(xiàn)在人們都是躺在蜜罐里生活,吃、穿不再湊合,講究“品味”成了主流,吃的營養(yǎng)、穿的時尚、過的小康已是普遍,包谷面饸饹或許成了過時黃花,成了生活的過去式。對于60年代的人來說,骨子里刻著鄉(xiāng)愁,血脈里流淌著苞谷、紅苕的汁漿,對于曾經吃到的包谷面饸饹,總覺得是饑餓時的奶酪、貧窮時的蛋糕,哪種滿足和解饞,終生難忘。
小時候在鄉(xiāng)下就讀過類似《人生》的小說,因此常把家鄉(xiāng)和小說里的山區(qū)做一比較,不同的是,我的家鄉(xiāng)沒有窯洞、山洞,沒有山茆丘壑,沒有鼻音較重或是、n、l、zhi、zi不分的語音。所謂的饃,就是壓制饸饹的面疙瘩,但這絕非隨意的去蒸。因為,蒸出來后,面疙瘩還要軟、粘、恰到好處地熟;過熟壓不出饸饹,過生壓出來的是斷節(jié)節(jié);同時要造型,因為壓制饸饹過程好比舂米的石臼原理,放置面疙瘩的是15公分深的圓形凹槽,“饃”就得揉成高10公分、直徑6公分的圓柱形,便于裝填。“饃”過大,壓制時多余的面溢出,糟蹋且不好收拾;“饃”過小,壓制出的饸饹又短又不豐滿,因此在壓饸饹前,都是各家取經,相互指導。壓制時多做一點,供他人品嘗或贈送。
咯咯吱吱的木頭擠壓聲,就是壓饸饹器具里出饸饹的聲音。饸饹有秩序地排列在篦子上,冒著熱氣,這時還不能急著吃,因為其它的“饃”不能等,涼了硬的就壓不成饸饹了,同一時間段里全部壓制結束,才算一頓饸饹壓完。吃饸饹時,熱的稍微有點甜,但有蔥花、熟油、油潑辣子助香,饸饹一下子就爽滑、勁道、軟香,尤其加點小菜,那種滋味簡直是炊煙彌漫飯飄香,一份美饌暖心潮。頓時,看生活,喝那紅苕苞谷珍,只覺得特別甜。